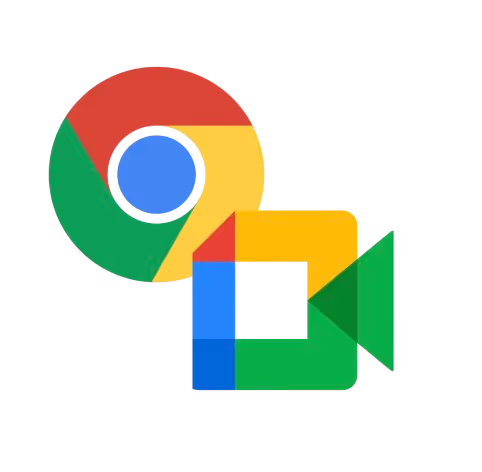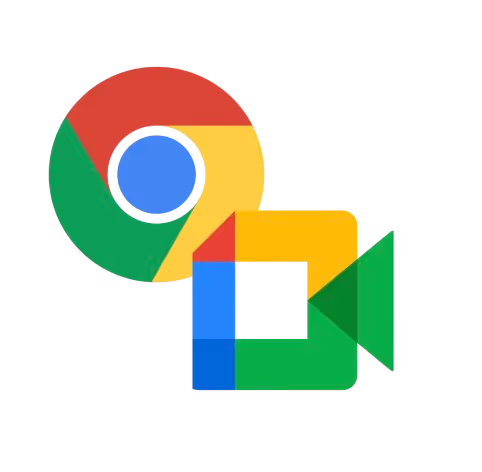我之所以如此投入打破语言障碍,不仅仅是我在东京担任产品管理职位的需求,在那里,我经常发现自己弥合了日本销售团队和讲英语的工程师之间的沟通鸿沟。这项使命深深植根于所谓的童年创伤。
我出生在台湾高雄,将普通话作为我的母语。但是,出生后不久,我移居日本,日语很快成为我的默认语言。小时候,我记不起自己对这种早期语言切换的感受,但它很可能为我将面临的挑战奠定了基础。
我与语言障碍的真正斗争始于我在加利福尼亚上小学。由于不懂英语,我发现自己无法与任何人交流。成为唯一的亚洲学生加剧了我的孤立感。在妈妈来接我之前,我大部分课都在睡觉,一无所知,没有朋友,孤身一人。
回到日本后,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我在美国吸收的个性和思想自由与日本的文化规范相冲突。这导致我被排斥和欺负,不仅受到同学的排斥和欺凌,也被老师排斥和欺负。由于缺少与我的混血背景和西方思维方式相同的朋友,而且父母都忙于工作,我完全孤立无援。
我在英国读高中和大学的旅程仍在继续,需要再次调整——这次是英语和英国文化,这与我在美国的经历有很大不同。这个过渡期充满挑战,但最终我找到了与我一样的文化流离失所感和归属感的国际学生的慰藉。
通过这些经历,我逐渐意识到语言障碍的深刻负面影响。它们会助长孤立、误解和缺乏沟通,从而升级为歧视和种族主义,从而使我们的工作甚至生活完全灰心丧气。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忍受着与这些障碍相关的痛苦和挣扎。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在乎打破语言障碍呢?答案在于我一生所忍受的痛苦,这是一种不懈的努力,以确保其他人不必像我一样面对同样的困难。